注:这是我为何帆教授第四本《变量》撰写的书评。在2019年,何帆兄发下大誓愿,要在未来30年每年写一本基于中国社会现实调查的书,直到建国100周年。受何帆同志激励,我也发下一个小誓愿,在未来30年内,每年都为何帆同志的《变量》撰写一篇书评。其实,我是有私心的。何帆兄每年用半年时间调研写成的书,我花几天时间读完,再花半天写就书评,其实是沾了何帆兄的光,借他的视角与笔触来与中国社会的基层与前沿对话,这对于我们从事经济研究的人而言,实在是一大幸事,每年值得浮一大白。点击文后的链接,可以查看我为何帆《变量》系列撰写的前三篇书评。文中配图摄于成都露天音乐广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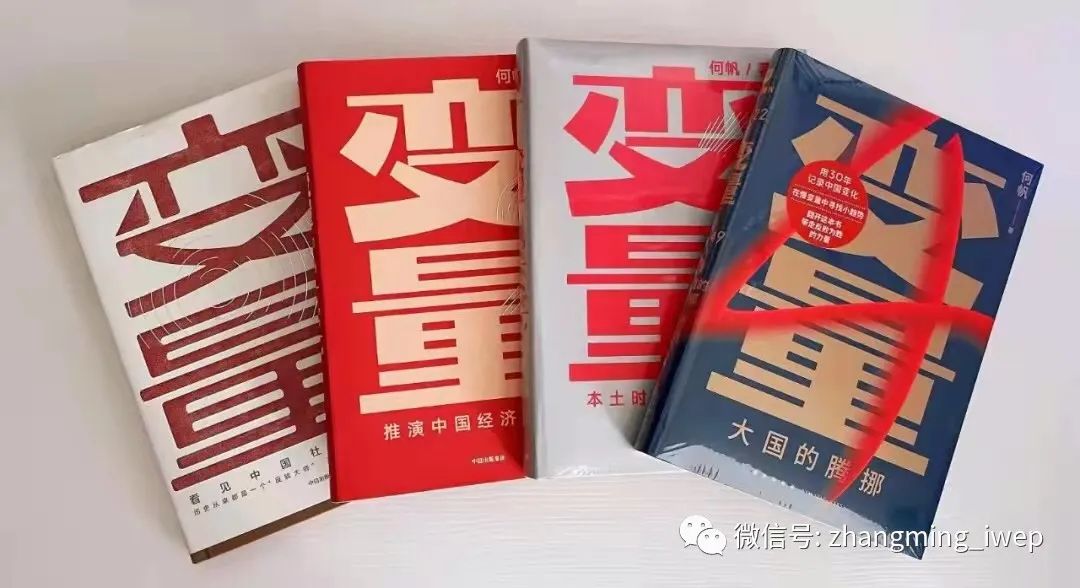
“记录历史,原来并不是调查坚硬岩石做成的纪念碑,而是描摹荡漾在水面上的浪花。每一朵浪花都曾努力闪烁过太阳的光芒,然后倏忽消失不见。我已经知道,这本书的宿命也是一样”。
这已经是何帆教授的第四本《变量》,这也是我撰写的第四篇《变量》书评。读完整本书后的一个感觉,是这本书既延续了此前三本《变量》独有的风格——也即从生动具体的故事中总结出耳目一新的道理,最后再赋予这些道理宏观或者历史的意义,但也有一些变化,描述心情、铺陈排比的句子多了不少。这说明何帆同志不是变得更加多愁善感了,就是心态变得更老成因此也更易起波澜了。
《变量4》的主题是大国的腾挪。“腾挪”是一个围棋术语,讲的是在局部处于不利地位时如何反败为胜的方法。何帆通过描述一盘2010年李世石与孔杰对弈的名局,来生动地说明了腾挪的效用。本书试图通过各种鲜活形象的案例来说明如何使用“腾挪”策略,并将其拆解为三大招式:寻找破局点、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改变约束条件。
竞争总是多维度的,所谓寻找破局点,就是把自己的优势资源集中在独特的一点,从而形成与竞争对手平等对峙的局面,并耐心等待反转的机会。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是指不要随波逐流,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套打法、培养自己的有生力量,而不是被动地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时间是有弹性的,你不可能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通过创造新条件、发现新契机,你可以找到迂回地解决问题的巧妙方法。对于试图在书中寻找心灵鸡汤或灵丹妙药的读者而言,读完上面这段话就可以把本书束之高阁啦。然而,《变量》这套书的最大特色在于,真正有趣的东西点缀在铺陈的细节中。
书中讲到的关于破局点的一个小故事,发生在浙江丽水松阳县四都乡陈桥铺村。一个非常偏僻的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古村里居然开了一家满载诗集、小说、艺术、哲学、历史、社会学书籍的先锋书店。如此高冷的书店开在一家惊艳的民宿里,而做民宿的小哥居然直言住在大城市里的人没见过世面。这家睥睨游人的书店就是一个告诉游客的宣言,在精神世界里,乡村要比城市更高一等。事实上,这家书店的开设也为陈桥铺村价格高昂的民宿做了一个恰到好处的背书。何帆谈到,破局点的选择至关重要。一方面,破局点首先是一个千斤顶,一定是你做得最得心应手的事情,能让你用相对较小的努力,释放更大的优势和被长久压抑的潜力。另一方面,破局点也最好是对手的一个失衡点,也即对方的力量配置与其自身能力之间的失衡,或者对手目标与现实之间的失衡。
关于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书中讲到的例子是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战略差异。国民党的战略是夺取重要城市和控制交通线,而共产党的战略则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聚焦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毛主席的一句话非常生动地说明了上述策略的精髓:“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国共两党在战略选择和局势判断上的差距,本质上在于他们对实力的认识不同。正如书中所言,“共产党一路都是艰苦创业,从未奢望能一把牌翻身,也不会奢望每一局都赢。他们更在意的是有没有留下足够的底牌,还能不能坚持下去。正是因为他们并不刻意追求局部的最优解,才无意中求出了全局的最优解。共产党算的是总赢率,也就是到了最后一局还能胜出的机会”。这一判断无疑是相当深刻的。
关于改变约束条件,本书基于步鑫生、马胜利等历史上改革能人先赢后输的例子,以及乡镇企业在特定时期内异军突起的案例,提出了以下重要判断:想要满足每一个约束条件,又想要求出最优解,这是一种危险的思路。很多时候问题没解决,不是因为目标函数不清晰,而是因为搞错了约束条件。在很多时候,如果问题现在解决不了,那么不妨放松时间约束,先拖着,等待时机成熟再来解决。而拖着的同义词,实际上也就是腾挪。此外,要解决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只能从具体情境出发,而非从我们熟悉的那些抽象原则出发。换言之,约束条件要比目标函数更重要。
从书中列举的关于县域生态崛起、小镇青年成功找到自己定位的大量例子,作者试图传达出如下观念,即对于一个企业、一个国家而言,当遭遇效率下降、制度僵化的难题时,要想避免衰落的宿命,就必须学会腾挪。所谓腾挪,就是要让组织内部的成员具有双重关系,既隶属于大组织,也隶属于小组织。通过成员在小组织内部的迁移与运动,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与重塑组织活力。这样的腾挪机制具有三大好处:一是个体有更多的选择空间,也能保持多元身份;二是小组织变得更有活力,也能享受多元化红利;三是大组织变得更加稳定,也更容易获得演化优势。这不由得让我联想到,近期中央出台了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与要素价格市场化的相关文件,何帆书中关于“腾挪”战略的描述,与这批文件的蕴意其实是不谋而合的。但毫无疑问,只有自身体量大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充分利用腾挪的好处。腾挪实则是为大国、大企业、大组织量身定制的工具。
我看过乐队的夏天前两季,我也对五条人乐队印象深刻。本书通过对五条人为什么能红遍全国的分析,得出了未来中国的创新更容易发生在边缘地带(例如县城相对于一线城市)的结论。这是为什么呢?一是因为边缘更加轻松、更加多元化,有着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养分;二是因为边缘的试错成本不高,大不了从头再来;三是边缘更适合混搭;四是边缘地带更容易找到新技术的应用场景。相比之下,大城市更容易无情绞杀很多才华和梦想。不过,正如五条人要在参加完乐队的夏天后才曝得大名一样,边缘的创新,终究要得到中心的认可、推崇和推广。边缘从中心受到熏陶,中心从边缘汲取营养,这才是一种可持续的、推动创新的良性互动。
通过对位于浙江嘉兴桐乡的桐昆集团开展智能化制造实践的调研,何帆教授指出,未来企业发展的方向未必是越大越好,因为大通常意味着垄断、傲慢、高杠杆与系统性风险,而“隐形冠军”才是最适应未来生态的物种。隐形冠军的特点通常是无聊、单调、平凡,但它们并不是不变,而是会用内部的微创新去对冲外部的波动。未来以大数据大资本为特色的互联网狂飙突进的“云时代”,可能演变为用大数据去整合供应链的“渠时代”。而BT(商务技术)人才将会成为最稀缺的人才,他们的任务是理解生产流程、了解行业需求,并将行业需求转化为IT技术问题,再将这些问题交给自己负责开发的同事。书中特意指出,这些年中国制造企业经历了各种惊涛骇浪,目前最关心的是供应链的稳定性:要有备胎、要有冗余、要考虑波动区间、要考虑进口替代、要加快技术创新。如果说在云时代企业家最关心的是如何才能赶上风口的话,那么在渠时代企业家最关心的则是如何才能穿越周期。
作为个人或者企业或者国家,如何才能穿越盛衰周期呢?这也是本书最让我击节的地方。何帆教授指出,在博弈论中有一种“从前往后看,从后往前推”的策略,也即你先一步步想到最终的赛局,找到为了赢得终局所需的策略,再一步步倒退回来,求出当下需要采取的最优策略。通过这种策略研判后发现,要成功穿越周期,你不能从众,不能依靠特权和地位,而要锻炼出一种不依附于任何系统、任何平台的生存能力。哪怕有一天只剩下你一个人,在旷野中振臂一呼,还有人愿意跟你走,那才是你的核心竞争力。对父母来讲,如果你考虑的终局不是孩子考上大学,而是孩子一生的发展,那么孩子最重要的能力包括养活自己的能力、终身学习的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快速进入一个陌生领域的能力、表达自我的能力、团队合作的能力,以及健康的体魄和心理。“逐浪人”想赢每一局,但正确的策略是追求总赢率。能留到最后,才有赢得终局的机会。诚哉斯言!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也提到中国如何运用腾挪的方式来应对地方政府债务与人口老龄化这两个棘手问题。总体思路是,我们不能仅仅把地方政府债务与老龄化人口看作是负债,也要把地方政府债务形成的基础设施以及老龄化人口看作是资产,通过盘活资产的方式来解决上述问题。例如,能否把高速公路沿线的零散土地、零散场房空地、服务区、收费站、通信管网、基站、广告牌等资源充分盘活?而要盘活这些资产,就必须改变土地使用性质与更多引入社会资本。此外,采用延长收费时间与采用更加灵活的收费方式(车少的时候少收费、车多的时候多收费),也能更好地盘活上述资产。又如,如果从资产端来审视人口老龄化,我们就能发现老龄社会蕴含的巨大商业机会以及老龄人口蕴含的巨大人力资本。在这一视角转换的基础上,何帆教授提出了三大猜测:一是我们将遇到局部的收入分配恶化与整体的收入分配改善(未来老年人内部的收入分配恶化值得关注);二是全球化退潮终将结束,新一轮的以劳动力跨国迁徙为特征的全球化浪潮将会再度兴起;三是越老越高比例的人口将会投入到越来越多的照顾他人的事务上来。如果上述大胆猜测成为现实的话,我们将会发现,老龄化社会也并非想象中那样灰暗。
总体来看,随着《变量》系列的演进,何帆教授的聚焦点在不断转变、叙事逻辑也在不断进化、讲故事的方法既一脉相承也推陈出新。这套书的最大特点,是在当前中国社会总量情绪较为悲观的背景下,作者不断地通过在微观领域发掘出来一系列创新来告诉读者,这是一个游戏规则转变、相对实力消长的大时代,要对中国社会微观主体的应急创新能力充满信心。书中的一个比喻让我印象深刻,过去我们持续处于爬山的过程中,视野里的风景有限。现在我们已经处于一座山的山顶,视野顿时开阔。即使前面还有不少山峰要攀登,但此时你的心情已经完全不同了。正所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不过,作为长期以来在酒桌上和何帆兄抬杠的师弟,我还是禁不住要在这本书乐观的基调之上再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大企业、大组织与大国都能够成功地运用腾挪的策略,来克服自身的效率下降与组织僵化,那么这些没能成功转型的组织可能出了什么问题呢?我想至少存在以下可能性:一是对外部的挑战与内部的问题存在不准确的认知,组织内部盲目乐观,被过去的成就遮蔽了双眼,忽视了进行腾挪调整的重要性与必然性;二是受到既得利益集团阻挠,内部各种要素流动存在或明或暗的障碍,不能充分流动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与重塑组织活力;三是组织的跨境要素流动出了问题。例如,在外部负面冲击下,原本应该进行要素的组织内部流动来应对冲击,但由于要素跨境管理出了问题,导致重要要素不是在组织内部流动,而是直接大规模流出组织。这样不但没能成功实现腾挪,反而直接引致危机。
我最后再举一个更加直观的例子。在当前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行、经济结构调整尚未完成、国内系统性风险防范化解依然在路上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应该审慎开放资本账户。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具备充分的腾挪空间在国内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但如果资本账户洞开,跨境资本可以自由流进流出,那么我们的腾挪空间将在极大程度上被压缩。适当的资本账户管制依然是我国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火墙,这道墙不能轻易拆除。
《变量:大国的腾挪》,何帆著,新星出版社,2022年1月版。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