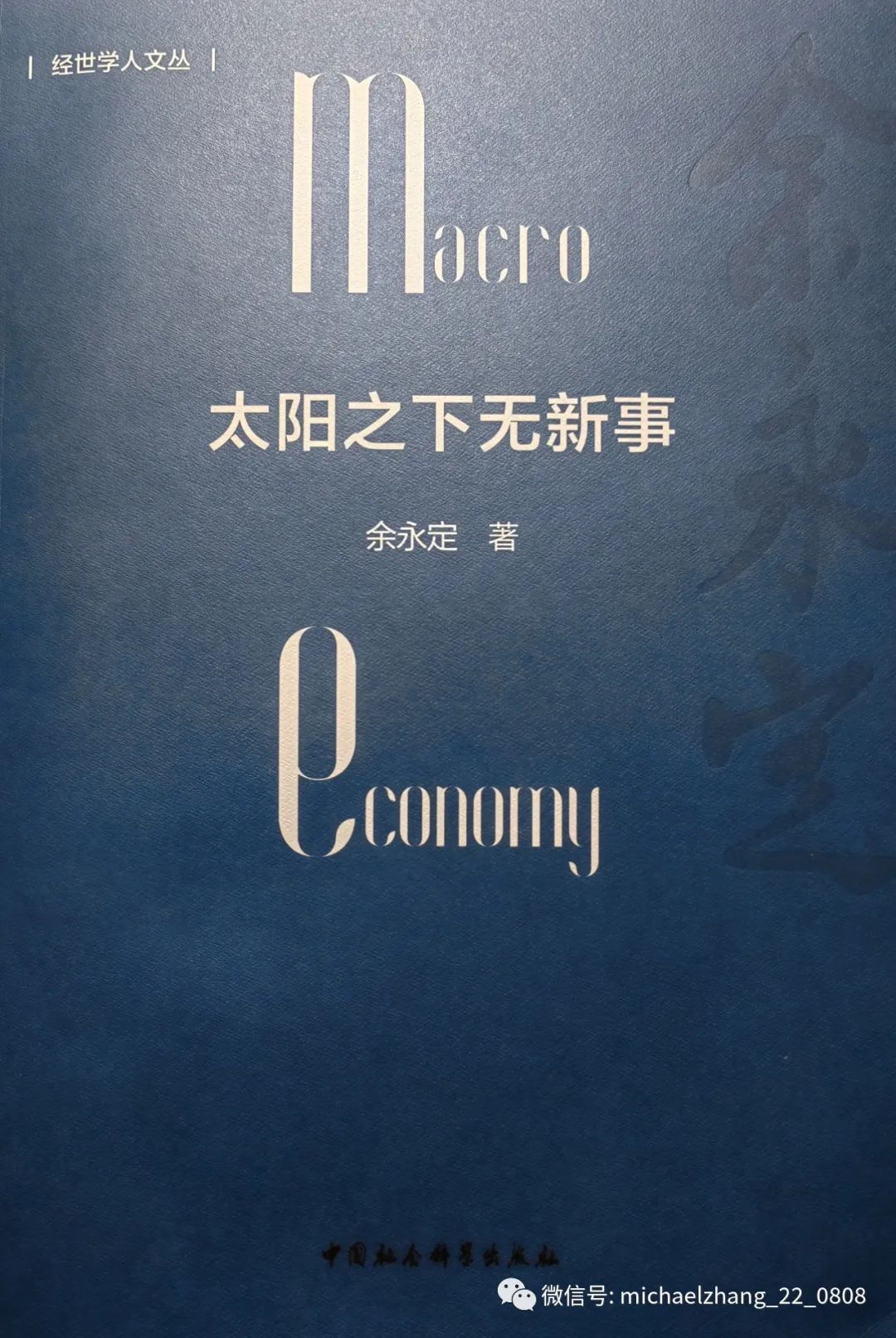
注:转载请注明出处,感谢陈胤默对本文的贡献。
我特别喜欢古龙的一本小说,名叫《七种武器》。我之前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年轻科研工作者的“七种武器”的文章。有一次,在我自己博士生的组会上,应同学们所邀,我把我的博士导师余永定老师学术研究的主要特点总结了一下,也梳理出了七点。当然,这个梳理仅仅是基于我个人长期以来跟随余老师学习与做研究的观感,不一定对,大家姑妄听之。
第一点,如果从学派划分的话,余老师是一个典型的凯恩斯主义者。
凯恩斯主义者的特点是什么呢?首先,他相信自由市场是有缺陷的。其次,他相信宏观政策总体上是有效的。当然,宏观政策有效有很多内在原因,例如短期内价格具有粘性、市场上各有关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与不完全等。
余老师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宏观经济学家。什么是纯粹的宏观经济学家呢?他基本上不太关注长期问题。这不是说长期问题不重要,而是指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短期上了。大家都知道凯恩斯有句名言,“长期内我们都死了”。
余老师这么多年跟踪中国宏观经济,他的一个主要诉求就是怎么通过恰当的宏观政策来消除产出缺口,尤其是消除负向产出缺口。他历来的观点是,潜在增速究竟是多少很难判断,但不能仅仅因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制造业产能过剩就认为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已经明显下降了。事实上,应该通过通胀指标的变动来辅助判断当前的产出缺口究竟是为正还是为负。
例如,这两年余老师在国内争议比较大的观点之一,就是他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推出的财政四万亿刺激本身没有问题。而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中国政府过早地退出了政策刺激。
余老师认为,如果短期的失衡迟迟得不到纠正的话,就会产生很多长期问题。一个典型例子是,一些人在短期内失业了,但由于当前技术进步很快,一旦失业时间足够长,想重新找到工作的困难度会越来越大。这就意味着短期失衡导致了长期结构性问题。
我跟余老师的观点也有一些分歧之处。例如,我一直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很感兴趣,这归根结底是个债务问题。但是,余老师觉得,只要增长足够快,短期债务问题没那么重要。
又如,余老师认为,中国政府应该为每年的GDP增长定一个稍高一点的具体目标。他认为GDP增速目标是一个有效的指挥棒,可以协调政府各个部门朝着这个目标共同努力。
第二点,余老师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一定要有独立的货币政策。
独立的货币政策指的是什么?首先,一国的利率水平应该是自由浮动的,且由国内市场供求来决定。其次,一国的汇率水平应该是自由浮动的,且由该国外汇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来决定。
换言之,IWEP宏观团队对利率和汇率市场化一直有着根深蒂固的信仰。但与此同时,因为中国是一个新兴经济体,国内金融市场还不够完善。人民币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的前提是不能让其大起大落。要防止利率与汇率超调,就必须搭配以适当的资本账户管制。异常的短期资本流动会对不够完善的金融市场产生很大扰动。事实上,凯恩斯也是反对短期资本自由流动的。
对大国独立货币政策的信念,决定了我们团队在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方面观点比较激进,而在资本账户开放方面观点较为保守。
第三点,余老师始终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应该大量借钱给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
这其实是余老师对经常账户的观点。他认为,中国长期持续的经常账户顺差是一个很大的失衡。过去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再叠加央行对汇率升值速度的限制,导致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而大量的外汇储备既是一种扭曲,也是一种资源浪费。
如何消除上述扭曲呢?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汇率自由浮动。汇率变动既会通过改变进出口来直接影响经常账户余额,也会通过改变国内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的相对价格来引导资源配置。另一种是消除国内居民、企业与政府部门存在的一些结构性失衡。
第四点,余老师相信历史会不断重演。
经济周期总会循环往复。因此,要做好宏观研究,就要对过去的历史数据和相关案例非常熟悉。虽然事情不会完全重复,但总会押着相似的韵脚。余老师的著作《太阳底下无新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这就是为什么做宏观研究需要长期经验积累的原因。你至少要经历两到三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你才有资格和底气来对未来做出判断。这也意味着宏观经济分析很难速成。
第五点,余老师非常尊重国外经验,但他绝不迷信发达国家。
余老师跟很多国外政要、经济学家、银行家有密切交流。他非常喜欢向他们问一些细节问题。例如,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余老师花了很多时间了解什么是CDO、CDS,其具体构造与风险特征是什么。他非常注重对问题细节的把握。
虽然余老师是在英国读的博士,但他对美欧很多所谓的信条,比如说华盛顿共识等,并不太感冒。从这一角度来讲,他认为不同国家很可能适用不同的经济模式。很多时候,他更加重视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经验教训。
第六点,余老师非常重视实地调研。
作为一个宏观经济学者,他不迷信任何学术权威,而是非常重视实地调研。除去实地调研之外,余老师经常给我在一些实际部门工作的师兄弟打电话,问他们在各自领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问题问得非常细致。
这其实是社科院学者的共同特点。他们对实地调研很重视,这使得他们看问题要比学院派经济学家更加深入。一方面能够抽丝剥茧深入到细节,另一方面也很注重分析逻辑的严谨和缜密。
余老师也经常打电话给我,问我对一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其实他自己已经有一个完整想法,但如果你的观点和他不一样,他就会和你一步一步地推敲,看我们到底是哪个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我觉得每次跟余老师的讨论,自己都受益匪浅。
经过余老师的长期训练,我觉得我们师兄弟在逻辑推理方面还是比较严谨的,参加学术讨论和政策辩论心底有底气。
第七点,余老师高度重视复盘。
一位学者形成自己的分析框架固然重要,但分析框架经常是会错的。余老师经常承认,他对有些问题的分析出了错误。他把分析出错看作一种宝贵机会,可以回过头来完善自己的分析框架。究竟是推理的环节出了问题,还是之前忽视了一些重要现象?知道哪里出错之后,你就可以进行修补。
只要对宏观问题敢做判断,那么出错是必然的事情。预测错误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错误进行复盘,避免未来犯同样的错误。在这一方面,余老师值得我们学习。
最后,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说明余老师非常强调对概念的准确把握。
当年,余老师很喜欢给想读他博士的学生出一道国际金融的题。即在真实世界里,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中的BP曲线会朝哪个方向倾斜?
IS-LM-BP曲线位于产出与利率构成的二维坐标轴中,BP曲线刻画了资本流动的均衡。试想,如果一国产出上升,那么该国的进口就会增加,这会导致该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那么该国如何实现国际收支再平衡呢?该国可以适当提高利率来吸引短期资本流入。以上分析意味着,如果一国产出上升,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该国利率也会相应上升,这就意味着BP曲线是应该向右上方倾斜。
如上所述,余老师非常强调对基本模型与基本概念做细致而扎实地把握。这样在参加学术讨论与政策辩论时,就不容易犯逻辑错误。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